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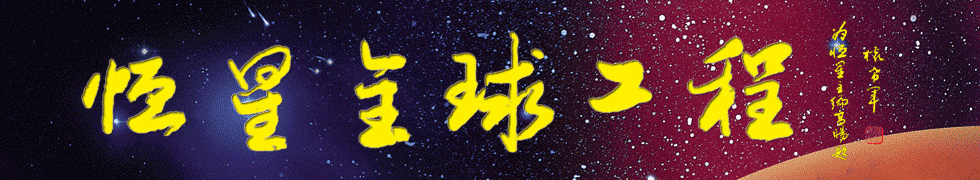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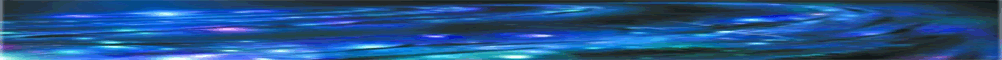
“对于具有追求阳光那样坚强思想的人来说,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早晨”——我喜欢这句话。
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一个光明的自我——清清白白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当“官”,连梦也是清晰的。
我只做一个梦——把一汽推向轿车时代。所以,我抓紧每一个早晨。
早晨,可能产生最美好的时空观。时间、效率、企业发展机遇的亮点,都可能在早晨寻找到。所以,我常常忘掉什么是黑夜。
联结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是学习和奋斗。
夕阳告别了我们。但是,明天,朝阳仍然会从东方升起。
——耿昭杰1992年3月
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
1985年6月,耿昭杰出任了这家具有光荣历史、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厂厂长。就是这个个子不高,看上去像个潇洒自信的学者的耿昭杰,在他上任后的短短8年里,借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一汽掀起了产品换型、技术改造的滚滚波涛。他不懈地探索着企业发展的每一个机遇,最终成为让一汽人自豪,让企业界钦佩,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的优秀企业家。短短的8年中,他凭着夷险取胜的胆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率领一汽10万员工劈波斩浪,艰苦创业,使一汽彻底甩掉了老式解放牌卡车30年一贯制的帽子,完成了一套从中型车更新换代到生产轻型车、生产轿车的“三级跳”高难动作。8年中,他凭着出众的工作成绩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等称号,并被推举为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一汽在他的领导下,跨进了国家一级企业行列,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
1988年6月,全国知名企业家云集一汽,召开“企业家与企业发展”研讨会,邀请耿昭杰作了题为《企业家与风险》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第一次阐述了对企业家概念的理解。他说:企业家就象艺术家、科学家一样,应该是办企业的专门家。他拥有从事管理企业所必备的知识、能力、阅历以至心理素质等条件,并且这一切都能在与风险搏斗中经受检验。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管到哪个企业都能玩得转,象职业教练员似的,可以受聘于任何一个队。
这段话,可以说是耿昭杰驾驭一汽这艘大船,闯过了一个个惊涛骇浪之后的经验之谈。人们把它称为耿昭杰给企业家下的定义。他之所以能如此准确地阐述企业家的内涵,是因为他尝到了管理企业的酸甜苦辣,在风险中磨炼了胆识、毅力,并且在攀登险峰与化险为夷的激烈搏击中,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企业发展之路。这条路,使闭塞30年的一汽通向了世界。外国人也知道了耿昭杰的名字,尤其是汽车业的老板们已感到了他那巨大的搏击风险的力量和强烈的竞争意识。
当代国际汽车工业的两位巨子,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前董事长雅科卡和德国大众公司董事会主席哈恩博士,曾相继专程飞赴长春,会见这个咄咄逼人的汽车业后起之秀。雅柯卡高举酒杯,诙谐地说:“耿先生,用我们美国人的话说,你是一个天生干汽车的家伙。你血管里流的都是汽油。”哈恩博士说:“耿先生是位真正的企业家,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是一流的,他是我们大众集团真正的对手和伙伴!”国人称赞他,外国同行也赞许他。那么耿昭杰,这个给企业家下定义的人,其成功的奥秘何在呢?
夷险取胜
夕阳告别了我们。但是明天,朝阳仍然会从东方升起。
1935年,耿昭杰出生于安徽巢县。1954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来到正在兴建中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从技术员、工程师逐步成长为一名既懂技术,又谙管理之道的企业领导人。历任铸造厂党委书记、汽车研究所所长、一汽党委副书记。
1985年6月,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担任了一汽的第6任厂长。此时的一汽,虽然表面上是一片升平,但却潜藏着巨大而深刻的危机。转过年来,这种危机便很快变成了现实。已生产了30年的老“解放”出现了全国性的市场滞销,上万台的积压车辆停放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任凭风剥雨蚀;规模宏大的换型改造工程由于失去了自筹资金的支撑,实际上已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面对环生的险象,耿昭杰经过缜密的权衡和思考,果断地提出了“单轨垂直转产”的大胆设想,即老“解放”全线停产,新产品全线上马。他的想法一经提出,立刻在领导层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厂转产新车都是采取新老车型平行生产或分总成过渡的方式,这样风险小,万一新车型转产失败,还有旧车型保驾,而垂直转产的同义词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这样干简直是在冒险。一旦失败,企业必然进退维谷。
还有一笔帐要算。有关业务部门交给耿昭杰一个死底:新车投产后,没有年产4万辆保底,别说上缴利润,就连职工工资也发不出去;而要完成上缴利税任务,年产量必须达到6.8万辆。这个数字是新车型CA141的最高设计能力。若当年达到最高设计能力,这在汽车工业史上也属罕见。
这是耿昭杰有生以来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抉择。这位曾当过汽车研究所所长的耿昭杰,知道这个抉择的分量。平行转产,生产出来的老汽车没人要,还要继续积压,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这毕竟是一条没有风险的路,许多人都会选择它;垂直转产,一年需走完国外一般七八年才能走完的路,且新产品达到国际水平,使企业一下子摆脱困境,这的确是一条希望之路。然而,这也却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险路。
耿昭杰开始集思广益,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群众的智慧来科学地论证第2条道路的可行性。经过反复论证和测算,他毅然把自己的家庭、荣辱、官职置之度外,选择了第2条风险之路。因为他相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这一古训。
耿昭杰曾说:企业家命中注定要伴随着风险过日子,这是他的职业特性。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要想战胜对手,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迎接风险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和企业家是一对孪生兄弟,风平浪静成就不了企业家。正因为如此,企业家自我完善的首要课题是正确对待风险,树立起自己的风险观。
1986年春节后的大年初六,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正门前的广场上,万名职工神情肃穆地站立在那里,凛冽的寒风在呼啸,人们的热血在沸腾。厂长耿昭杰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庄严地发布了换型决战的动员令:“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这高亢的声音撼动着一汽20余万职工和家属的心。“厂兴我荣,厂衰我辱”,这是一汽职工对厂长发布动员令的最有力的回应。个人收入减少了,职工没有怨言;夜以继日地苦战,无人计较报酬。耿昭杰也和职工一样,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这期间家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直到他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时,他妻子不知是喜,不知是忧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这回总算有个‘家’了。”
1986年9月29日,最后一辆老“解放”——第1281502辆车缓缓地开下总装线。一汽的一个沉重的时代结束了。
1987年元旦,CA141新型解放牌汽车英姿勃勃地开出总装配线,当年产量即达到了6.8万辆的设计能力,质量达到国家一等品的水平。一汽的又一个青春的时代开始了。
目睹一汽冲出险区,获得新生,耿昭杰平静地说:“我之所以最欣赏夷险取胜的精神,只因为风险往往是与美好的前景连在一起的”。
战略兼并
对于具有追求阳光那样坚强思想的人来说,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早晨。
在一汽,耿昭杰有个外号叫“耿着急”,这不仅因为他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而更多地则表现在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认准了的事,就非干不可,并且一定要干成。他不允许自己,也不允许他的部下不讲效率,更不允许一汽这个大企业成为一条四平八稳的老黄牛,在旧体制的轨道上晃晃悠悠。
一个人的进取精神达到一定高度,就会对自己的事业永不满足。为了尽快改变中国汽车工业缺重少轻的生产格局,在中型车换型决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耿昭杰又把6万辆轻型车基地建设的重担压到了自己的肩头。项目拿到了,又一个两难选择尖锐地摆在了耿昭杰的面前。整个工程需投资10亿元,一汽换型刚刚结束,元气尚未恢复,要上,这样一大笔投资如何筹集呢?等资金,一汽产品结构单一的状况何时才能改变,单纯靠中型车一汽何以得到发展?干,没有资金,也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干好。在耿昭杰的工作程序中,向来就没有“等等看”这个词汇。
对国际汽车工业发展规律的深邃研究,使耿昭杰深切地感到,一汽的轻型车要做到高起点、大批量和专业化,必须通过联合和兼并,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做到少投入,快产出。
机遇对于善于利用它的人是永恒的。当时,吉林省和长春市共有4个生产轻型车的主机厂和总成配套厂。由于产品落后,市场无销路,这几个厂的生产经营已经到了难以维继的地步,迫切希望背靠一汽这棵大树,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一汽又有成熟的整车和从国外引进的发动机产品及制造技术,如果二者有机结合,轻型车基地建设就会如虎添翼,很快起飞。关键是能否突破“三不变”体制的束缚,把这几个企业紧密联合到轻型车生产联合体中来。
耿昭杰和他的谋士们绞尽脑汁,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名为“投资入股分利”的最佳联合形式。即地方政府把几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一汽,而企业的原有固有资产作为地方对一汽的投资,一汽则以产品、技术和管理软件及部分补充资金作为投入,双方按投资比例参加利润分配,企业原税收渠道不变。由于这种方式巧妙地摆脱了“三不变”的制约,又充分照顾了地方的利益,因而深受地方政府和这几家企业的欢迎。据有关专家测算,通过这种建设方式,大大加快了轻型车基地的建设步伐。一汽的轻型车工程至少节省投资两个亿,同时还缩短了建设周期。凭靠有偿兼并,1992年,一汽已有6000余辆1.5吨卡车和11座面包车投放市场,其产品的水平、造型和各种性能在当今国内轻型车市场上都是佼佼者。耿昭杰手中又多了一种强有力的竞争武器。
忧患意识
联结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是学习和奋斗。
在耿昭杰给企业家下的定义里,并没有忧患意识这一条。然而,这正是中国企业家与众不同的特色。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企业家忧国忧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把中国企业家与西方企业家相比,一个外国企业家只要能赚钱,可以不考虑其他。而中国企业家,双肩上不但要承受外国企业家那样管理企业的全部担子,而且还要肩负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面临旧经济体制的挑战,习惯势力的挑战,社会不正之风的挑战,远比一个西方企业家面临的挑战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中国企业家少的是自主发展的政策和条件,多的是责任和奉献。
1954年,耿昭杰刚刚到新建的一汽时,是个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技术员。一汽试制轿车,他参与了轿车上的一个小电机的测绘与设计。那时他想能亲手为生产中国的轿车出一点力,该有多自豪啊!因此,他经常工作到半夜。不论多晚,回宿舍之前,他总喜欢走到轿车的油泥模型面前,细细品味一番。那时一汽人,为了造出为国争光的国产轿车,拚命拚得近乎“迂腐”。没有样车,技术人员长途跋涉,跑到本溪钢铁厂,从钢铁垃圾山上翻找进口汽车的零部件作参照物,搞出自己的设计;没有大型覆盖件的冲压模具,能工巧匠就一锤一锤地敲出轿车的外壳……就这样,终于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辆东风(后改名为红旗)牌小轿车。那时,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的轿车工业江山依旧,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既难以满足轿车高新技术的要求,又难以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而在此期间,国外的轿车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汽车工业大国日本暂且不说,比我们起步晚10年的韩国也远远地把我们抛在了后面。80年代中期,大量国外轿车,特别是日本车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国市场。
一位日本商人来到北京,刚下飞机乘车驶向下榻的饭店时,不无讽刺地说了句:“我感觉象是又回到东京了,因为满街跑的都是日本车。”听了这话,耿昭杰象被打了一个耳光,热血上涌,愧疚良久。身居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作为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之题写奠基碑文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长,耿昭杰感到愧对江东父老。正因为如此,他从上任那天起,便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中国的轿车工业搞上去,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即使是在换型改造最紧张的时刻,轿车的研制和开发也始终没有停止。他在积蓄力量,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1987年5月27日。中国轿车之战的序幕拉开了。国务院决策咨询小组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召开了轿车发展的战略研讨会。
这是一次规划大政方针的会,同时也是一次争项目的会。出人意料,耿昭杰在会上作了一个低调子的发言。他认为,中国的轿车生产不应该首先着眼出口,而是要先占领国内市场,占领国内市场本身就是参与了国际竞争,他率先打出了挡住进口的旗帜。他还认为,中国的轿车工业要上,必须充分发挥现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作用,不宜新铺摊子,再建新点。他的发言充满了清醒的务实快上精神,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
七届人大小组会上他侃侃而谈:“到目前为止,我国轿车保有量已达28万辆,其中80%%是进口货,为此国家耗去了相当于建设22个一汽的投资。再不采取措施,到1990年,这批轿车进入更新期时,轿车进口的狂潮将再次席卷我中华大地,我国民族汽车工业将再度蒙受耻辱”。
耿昭杰的几次重要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1987年8月,一汽正式被国家确定为国内三大轿车生产基地之一。为了加快轿车工程的建设步伐,耿昭杰又提出了“从中高级起步,向下发展;依托老厂,轻轿结合;一次规划,分期实施;先建成一个年产3万辆的先导厂,挡住进口,进而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设一个符合经济规模的年产15万辆的轿车生产基地”这一符合国情和厂情的一汽轿车发展战略。在那段时间里,他和他的助手们频繁奔走于欧美,进行产品选型,寻找合作伙伴。
6年过去了,人们惊喜地发现,在一汽老厂区西去数公里处,一座规模宏伟的轿车新厂区已拔地而起。在边投入、边产出、边提高国产化水平的原则指导下,一汽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建设的奥迪中高级轿车工程已基本建成,现已达到年产两万辆奥迪100型轿车的生产能力,国产化率已达40%;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合资建设的15万辆普及型轿车生产基地——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已经投产。1992年,它生产的高尔夫系列捷达牌轿车投放市场后,该公司已在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排名第188位。
耿昭杰的轿车梦已初步变成了现实。一辆辆红旗、奥迪、捷达轿车,满载着耿昭杰和一汽人那深厚的民族感情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去抵挡进口车的冲击,去传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1992年,耿昭杰开始对一汽逐步实行公司化体制改革,成立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按照决策、经营、生产三个层次相分离和生产经营与后勤服务部门相分离的原则,把过去的总厂——专业厂两级管理体制转变为总公司——分公司或子公司——专业厂三级管理体制,从而形成投资——利润——成本三级责任中心。随着公司化体制的变革,一汽的现代化管理正在攀上一个新高峰。这一年,公司共生产不同车型汽车13.7万辆,全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位居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第6名。
作为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耿昭杰不仅以自己的语言给企业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更以自己的规范行为和巨大贡献,描述了一位中国优秀企业家的内涵和外延。


